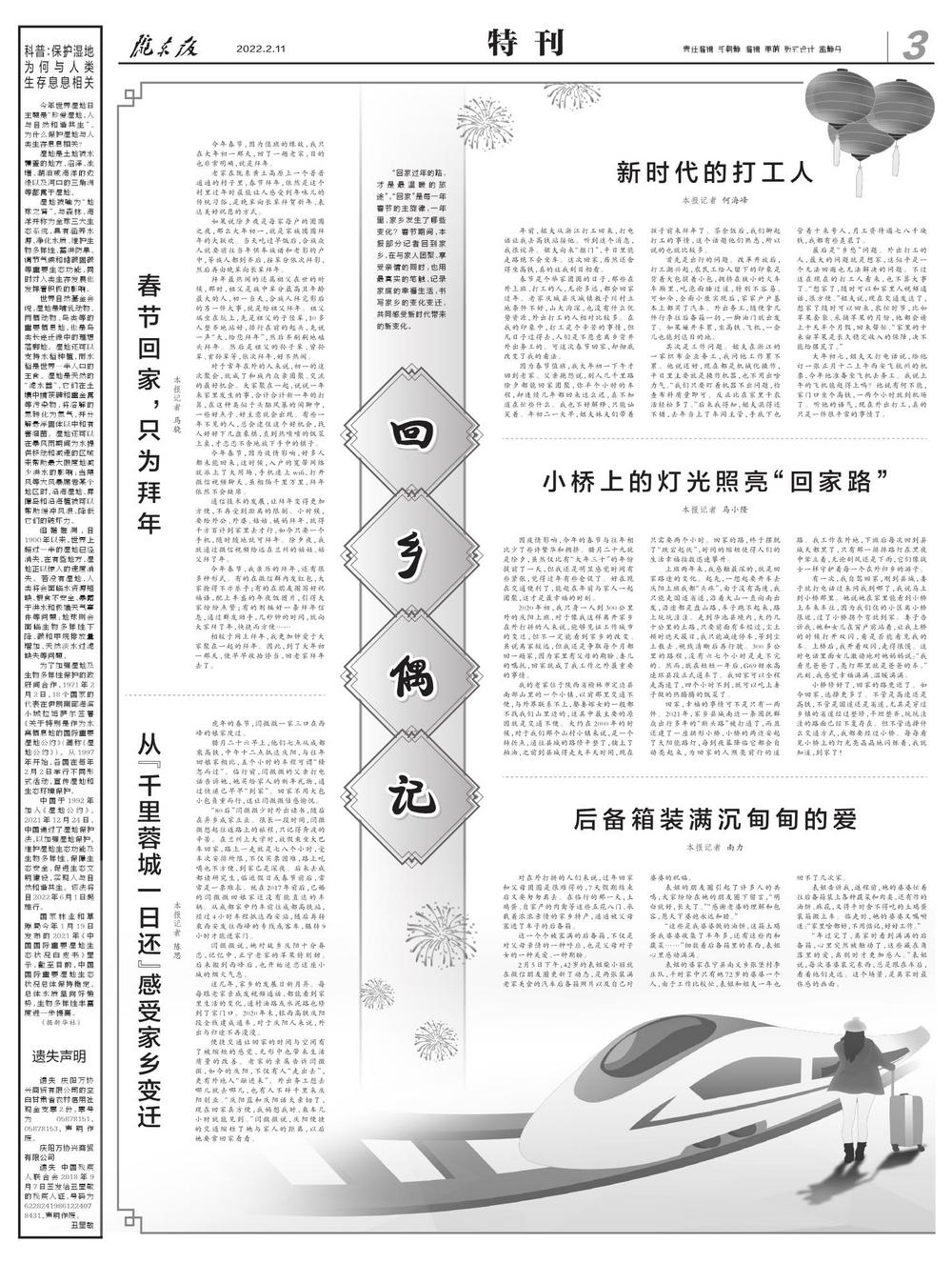本报记者 马骁
今年春节,因为值班的缘故,我只在大年初一那天,回了一趟老家,目的也非常明确,就是拜年。
老家在陇东黄土高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里,春节拜年,依然是这个村里过年时最能让人感受到年味儿的传统习俗,是晚辈向长辈拜贺新年、表达美好祝愿的方式。
如果说除夕夜是每家每户的团圆之夜,那么大年初一,就是家族团圆拜年的大联欢。当天吃过早饭后,合族众人就要前往当年供奉族谱和老影的户中,等族人都到齐后,按辈分依次拜影,然后再由晚辈向长辈拜年。
拜年最热闹的还属祖父在世的时候,那时,祖父是族中辈分最高且年龄最大的人,初一当天,合族人拜完影后的另一件大事,就是给祖父拜年。祖父端坐在炕上,先是祖父的子侄辈,10多人整齐地站好,排行在前的起头,先说一声“大,给您拜年”,然后齐刷刷地磕头拜年。然后是祖父的孙子辈、曾孙辈、玄孙辈等,依次拜年,好不热闹。
对于常年在外的人来说,初一的这次聚会,就成了和族内众亲团聚、交流的最好机会。大家聚在一起,说说一年来家里发生的事,合计合计新一年的打算,在这种类似于头脑风暴的闲聊中,一些好点子、好主意就会出现。有些一年不见的人,总会逮住这个好机会,找人好好下几盘象棋,直到热喷喷的饭菜上桌,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的棋子。
今年春节,因为疫情影响,好多人都未能回来,这时候,入户的宽带网络就派上了大用场,手机连上wifi,打开微信视频聊天,虽相隔千里万里,拜年依然不会缺席。
通信技术的发展,让拜年变得更加方便,不再受到距离的限制。小时候,要给外公、外婆、姑姑、姨妈拜年,就得千方百计到家里去才行,如今只要一个手机,随时随地就可拜年。除夕夜,我就通过微信视频给远在兰州的姑姑、姑父拜了年。
今年春节,我亲历的拜年,还有很多种形式。有的在微信群内发红包,大家抢得不亦乐乎;有的在朋友圈写好祝福语,配上丰盛的年夜饭图片,引得大家纷纷点赞;有的则编好一条拜年信息,通过群发助手,几秒钟的时间,就向大家拜了年,快捷而方便……
相较于网上拜年,我更加钟爱于大家聚在一起的拜年。因此,到了大年初一那天,便早早收拾停当,回老家拜年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