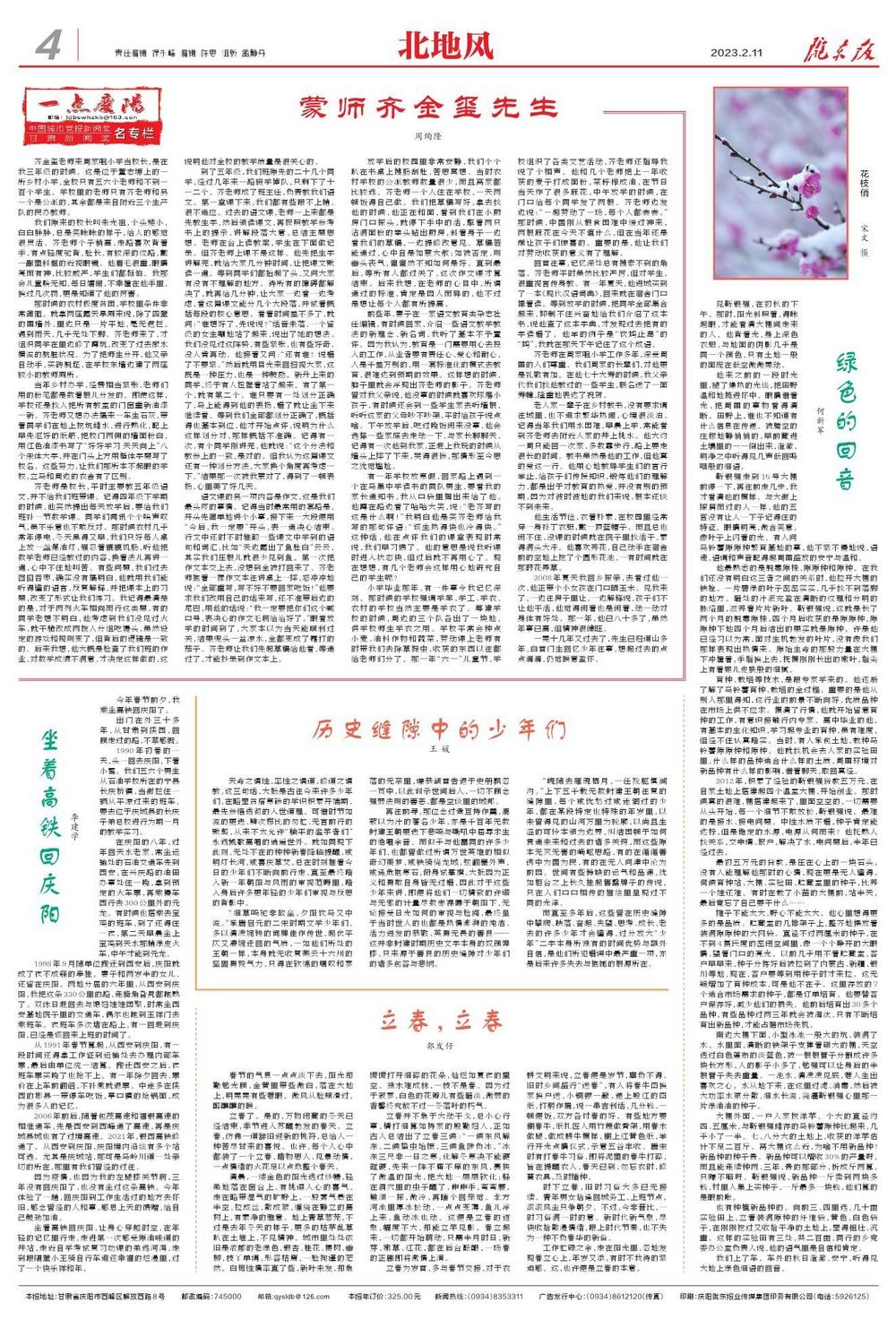周绚隆
齐金玺老师来周家咀小学当校长,是在我三年级的时候。这是位于董志塬上的一所乡村小学,全校只有五六个老师和不到一百个学生。学校里的老师只有齐老师和另一个是公派的,其余都是来自附近三个生产队的民办教师。
我们原来的校长叫朱光祖,个头矮小,白白胖胖,总是笑眯眯的样子,给人的感觉很灵活。齐老师个子稍高,走路喜欢背着手,有点轻度驼背,脸长,有较深的纹路,戴一副塑料框的近视眼镜。他眉毛很重,眼睛亮而有神,比较威严,学生们都挺怕。我那会儿童騃无知,每日嬉闹,不幸撞在他手里,挨过几次罚,更是知道了他的厉害。
那时候的农村极度贫困,学校里条件非常简陋。就拿两座露天旱厕来说,除了四壁的围墙外,里边只是一片平地,毫无遮拦。遇到雨天,几乎无处下脚。齐老师来了,才组织同学在里边修了蹲坑,改变了过去尿水横流的肮脏状况。为了把师生分开,他又亲自动手,买砖脱坯,在学校东墙边建了两座较小的教师厕所。
当年乡村办学,经费相当紧张,老师们用的粉笔都是数着根儿分发的。即使这样,学校还是找人把所有教室的门窗重新油漆一新。齐老师又想办法搞来一车生石灰,带着同学们在地上挖坑储水,进行熟化,配上早先沤好的纸筋,把校门两侧的墙面粉白,用红色油漆书写了“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”八个宋体大字,并在门头上方用楷体字题写了校名。这些努力,让我们那所本不起眼的学校,立马和周边的农舍有了区别。
齐老师是校长,平时主要教五年级语文,并不给我们班带课。记得四年级下学期的时候,他突然提出每天放学后,要给我们班补一节数学课。同学们闻讯个个唉声叹气,虽不乐意也不敢反对。那时候农村几乎常年停电,冬天黑得又早,我们只好每人桌上放一盏煤油灯,强忍着辘辘饥肠,听他把数学老师已经教过的内容,换着法儿再讲一遍,心中不住地叫苦。有些问题,我们过去囫囵吞枣,确实没有搞明白,他就用我们能听得懂的语言,反复解释,并把课本上的习题,改变了形式让我们练习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,对于两列火车相向而行这类题,有的同学老想不明白,他考虑到我们没见过火车,就干脆改成两拨人分组吃馒头,虽然设定的游戏和规则变了,但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。后来我想,他大概是检查了我们班的作业,对数学成绩不满意,才决定这样做的,这说明他对全校的教学质量是很关心的。
到了五年级,我们班原先的二十几个同学,经过几年来一路辍学掉队,只剩下了十一二个。齐老师成了班主任,负责教我们语文。第一堂课下来,我们都有些跟不上趟,很不适应。过去的语文课,老师一上来都是先教生字,然后领读课文,再按照教学参考书上的提示,讲解段落大意,总结主题思想。老师在台上读教案,学生在下面做记录。但齐老师上课不是这样。他先把生字讲解完,就给大家几分钟时间,让把课文默读一遍。等到同学们都抬起了头,又问大家有没有不理解的地方。待所有的障碍都解决了,就再给几分钟,让大家一边看一边考虑,看这篇课文能分几个大段落,并试着概括每段的核心意思。看着时间差不多了,就问:“谁想好了,先说说?”话音未落,一个留级的女生唰地站了起来,说出了她的想法。我们没见过这阵势,有些紧张,也有些好奇,没人肯再动。他接着又问:“还有谁?说错了不要紧。”然后就用目光来回扫视大家,这既是一种压力,也是一种鼓励。新升上来的同学,终于有人扭捏着站了起来。有了第一个,就有第二个。谁只要有一处划分正确了,马上能得到他的表扬,错了就让坐下来继续看。等到我们全部都划分正确了,概括得也基本到位,他才开始点评,说明为什么这样划分对,那样概括不准确。记得有一次,有个同学刚讲完,他就说:“这个分法和教参上的一致,是对的。但我认为这篇课文还有一种划分方法,大家换个角度再考虑一下。”结果那一次被我蒙对了,得到了一顿表扬,心里美了好几天。
语文课的另一项内容是作文,这是我们最头疼的事情。记得当时最常用的套路是,开头先简单地讲个小事,接下来一大段便用“今后,我一定要”开头,表一通决心结束。行文中还时不时堆砌一些课文中学到的语句和词汇,比如“天边露出了鱼肚白”云云,其实我们压根儿就很少见到鱼。第一次把作文本交上去,没想到全被打回来了。齐老师抱着一摞作文本往讲桌上一摔,怒冲冲地说:“全部重写,写不好不要回家吃饭!”他要求我们改用自己的话来写,还不准带后边的尾巴,用他的话说:“我一定要把你们这个喊口号、表决心的作文毛病给治好了。”眼看放学的时间到了,大家本以为当天能顺利过关,结果兜头一盆凉水,全都变成了霜打的茄子。齐老师让我们先起草稿给他看,等通过了,才能抄录到作文本上。
放学后的校园里非常安静,我们个个趴在书桌上搜肠刮肚,苦思冥想。当时农村学校的公派教师数量很少,而且离家都比较远。齐老师一个人住在学校,一天两顿饭得自己做。我们把草稿写好,拿去找他的时候,他正在和面,看到我们在小厨房门口探头,就停下手中的活,擎着两只沾满面粉的拳头钻出厨房,斜着身子一边看我们的草稿,一边提修改意见。草稿若能通过,心中自是如蒙大赦;如被否定,则垂头丧气,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。直到最后,等所有人都过关了,这次作文课才算结束。后来我想,在老师的心目中,所谓通过的标准,肯定是因人而异的,他不过是想让每个人都有所提高。
前些年,妻子在一家语文教育类杂志社任编辑,有时候回家,介绍一些语文教学教法的新理念、新名词,我听了基本不予置评。因为我认为,教育是一门需要用心去投入的工作,从业者要有责任心、爱心和耐心,人是千差万别的,用一套标准化的模式去教育,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。这样想的时候,脑子里就会浮现出齐老师的影子。齐老师曾对我父亲说,他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琢磨小孩子,有时候还会到一些学生家去听墙根,听听这家的父母吵不吵架,平时给孩子说点啥。下午放学后,吃过晚饭闲来没事,他会选择一些家庭去走动一下,与家长聊聊天。记得有一次他到我家,正赶上我玩的时候从墙头上摔了下来,哭得很惨,那情形至今思之犹觉尴尬。
有一年学校放寒假,回家路上遇到一个在马集中学读书的同队男生,要看我的家长通知书,我从口袋里掏出来给了他。他蹲在路边看了哈哈大笑,说:“老齐写的这是什么啊!”我明白他是笑齐老师给我写的那句评语:“该生热得快也冷得快。”这种话,他在点评我们的课堂表现时常说,我们早习惯了。他的意思是说我听课时进入状态快,但过后就不再用心了。现在想想,有几个老师会这样用心地研究自己的学生呢?
小学毕业那年,有一件事令我记忆深刻。那时候的学校强调学军、学工、学农,农村的学校当然主要是学农了。筹建学校的时候,周边的三个队各出了一块地,供学校师生学农之用。学校平常会种点小麦、油料作物和蔬菜,劳动课上老师有时带我们去除草捉虫,收获的东西以往都给老师们分了。那一年“六一”儿童节,学校组织了各类文艺活动,齐老师还指导我说了个相声。他和几个老师把上一年收获的麦子打成面粉,菜籽榨成油,在节日当天炸了很多麻花,中午放学的时候,在门口给每个同学发了两根。齐老师边发边说:“一起劳动了一场,每个人都尝尝。”那时候,中国刚从粮食困难中缓过神来,两根麻花在今天不值什么,但在当年还是颇让孩子们惊喜的。重要的是,他让我们对劳动收获的意义有了理解。
回首往事,记忆深处总有搜索不到的角落。齐老师平时虽然比较严厉,但对学生,很重视言传身教。有一年夏天,他进城买到了一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回来就在宿舍门口捧着读。等到放学的时候,把同学全部集合起来,抑制不住兴奋地给我们介绍了这本书,说他查了这本字典,才发现过去把有的字读错了。他举的例子是“饮鸩止渴”的“鸩”,我就在那天下午记住了这个成语。
齐老师在周家咀小学工作多年,深受周围的人们尊重。我们周家的长辈们,对他更是礼敬有加。在他七十大寿的时候,我父亲代我们找他教过的一些学生,联名送了一面寿幛,隆重地表达了祝贺。
老人家一辈子在乡村教书,没有要求调往城里,也不追求繁华热闹,心境很淡泊。记得当年我们用水困难,早晨上学,常能看到齐老师去附近人家的井上挑水。他大约一周只能回一次家,多数靠步行,路上要走很长的时间。教书虽然是他的工作,但他真的爱这一行。他用心地教导学生们的言行举止,给孩子们传授知识,锻炼他们的理解力,都是出于对教育的热爱,并没有别的预期,因为对彼时彼地的我们来说,根本还谈不到未来。
他生活节俭,衣着朴素,在校园里经常穿一身补丁衣服,戴一顶蓝帽子。而且总也闲不住,没课的时候就在院子里找活干,累得满头大汗。他喜欢养花,自己动手在宿舍前的空地上挖了个圆形花池,一有时间就在那莳花弄草。
2008年夏天我回乡探亲,去看过他一次,他正带个小女孩在门口晒玉米。见我来了,一边往房子里让,一边解释说,孩子们不让他干活,他觉得闲着也是闲着,动一动对身体有好处。那一年,他已八十多了,虽然年事已高,但精神很健旺。
一晃十几年又过去了,先生已归道山多年,白首门生回忆少年往事,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,仍觉暖意盈怀。